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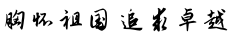
发布时间:2024-12-27源自:本站作者:admin阅读(69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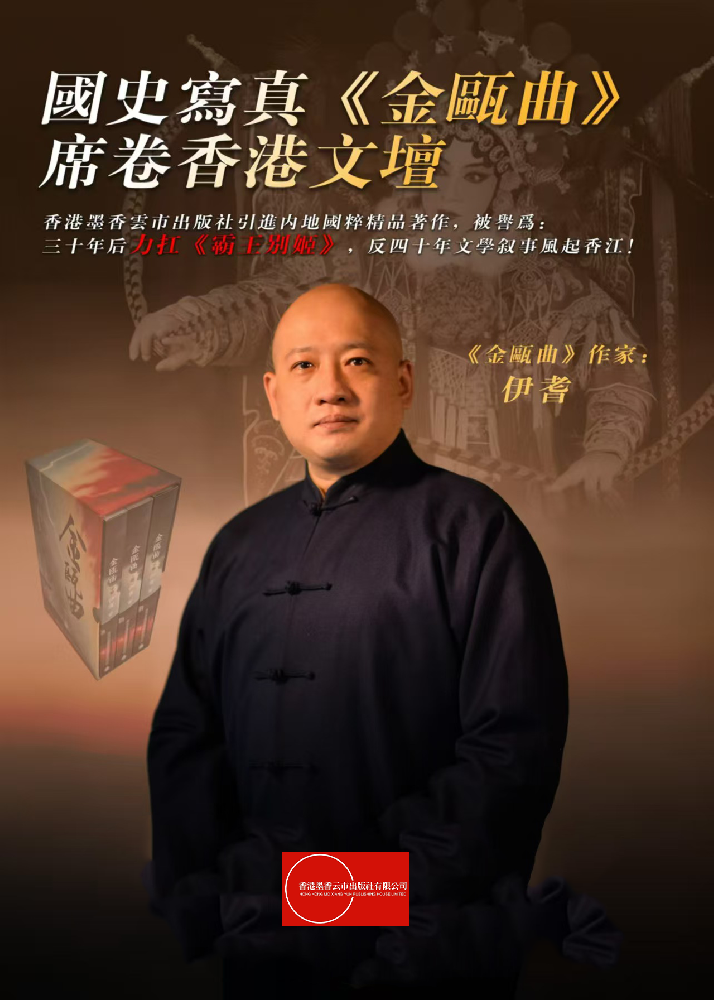
由香港墨香雲市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發行的長篇小說《金甌曲》近日上市,這部作品鎖定新中國成立前30年的歷史背景,以京劇題材為依託,對於那段歷史的敘事角度,與過往四十年來中國文壇的話語有著極大反差,作者試圖還原某部分被遮蔽的真相,帶領年輕讀者走進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,在現實與藝術的雙重構建中確立“文化自信”。有文藝評論家稱這部作品“三十年後力扛《霸王別姬》 ”,今天關於《金甌曲》,我們與作家伊耆展開如下對話。
1.為什麼會想到寫這樣一部小說?
伊耆:我是十多年的職業媒體人,長期深耕文化領域的報導,加上出身中文系,故而有機會接觸到眾多文化人、藝術家,也有和他們平等對話的能力,因此能夠獲得很多所謂“猛料”。這些行走過風雨人生的長者,願意把一生的經驗、反思、遺憾對我講出來,這裏面本身是故事寶庫,有太多可歌可泣、可資記錄的。多年前,一位飲譽海內外的藝術家對我說過一個人生總結:生於亂世、長於治世、成於盛世、流傳後世。這句話非常有穿透力,也是這句話喚醒了我的作家基因。
我本身是學習文藝理論的,也寫批評文章,搞創作不在我人生規劃中,是命運之手把我拋到了這裏。因為工作便利讓我接觸到了那麼多經歷傳奇、性格鮮活的人物,我覺得有必要把這些人、這些事寫出來。理論的說服力永遠不如故事來得真切,故事能最大化傳播,所以我決心用一部長篇小說來呈現自己的理性化思考。
2.這部作品你最想表達的是什麼?是否有現實人物原型做依託?
伊耆:承平日久,物質的豐饒、技術的發達讓我們的生活舒適度、便捷度達到了人類有史以來的高峰,但是人格的豐贍、人心的飽滿並不因此而同步增長,甚至在某些領域嚴重退化。我們今天還有多少體驗美的能力?還有多少體會愛的能力?還要多少“逃禪不借隱為名”的能力?還要多少願意相信的能力?
沒有一代人活得不艱難,其實就在不是很遠之前,中國人能夠活下去都是要費勁全力,亂世螻蟻不是文學的誇張,是血淋淋的現實。那位總結出“四世論”的藝術家告訴過我,小時候真的沒飯吃,家裏連一粒米都沒有,這還是在北京!在和這些老人接觸中,我發現了他們身上有一個共性,就是堅韌、達觀。
《金甌曲》的主人公有生活原型,但不是單一的原型,而是那一代人的共性挖掘。在我所接觸過的文化老人裏,他們不約而同認為50年代是最美好的年代,這裏固然有他們青春記憶的作祟,但更主要的還是因為那個時代的的確確有令人難以忘卻的記憶。我為什麼要把作品的時間線放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到改革開放伊始?新中國到底新在何處,我的體會是新在精神,1949年以後的中國人同此前的中國人,內心世界是兩個物種。如果不把這個問題講明白,那革命和歷史上王朝更迭就沒有本質區別。我從老紀錄電影當中也映證了這種看法,50年代國人的眼神透著一束光亮,對比晚清、民國時的照片,你一眼就能看出這兩種中國人有天壤之別。由於長期宣傳、教育的某種偏頗,對於我們沒有經過那個年代的人,一提起那時候就是和貧窮、封閉畫上等號,這其實是非常大的誤解。
與今天相比,新中國前30年生活條件自然是差的,但不要忘記我們從哪里來?我非常反感美化民國的論調,所謂的“民國範兒”不過是一小撮有產者的紙醉金迷,那不是真實的民國,山河破碎、賣兒賣女、餓殍遍地才是那個時代中國的真實寫照。1949年中國還處於農業文明,到1979年我們已經構建起初步完善的獨立工業體系,和西方世界的距離至少拉到了同一維度上,而不再是被人降維打擊。我們常說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奇跡,但歷史是貫通的,新中國前30年的發展也是奇跡,而這種奇跡的誕生,是整整一代人把生活水準降到最低,用血汗拼出來的。
再說封閉,近三四十年,我們的開放也伴隨著文化陣地潰敗,幾乎是西方文化單方面灌輸,中國文化走不出去,甚至連中國人自己都失去了文化自信。可就在並不富裕的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,中國的藝術家已經用文藝橋樑,搭通了我們與世界的接觸,而且是中國文化有力的輸出。書中的主人公帶領藝術團演了幾十個國家,從女王、總統到卓別林這樣世界影響的藝術大師,都被傾倒,這是鮮活的史實。1930年,梅蘭芳把京劇帶到了美國,但和新中國的文化交流無法相比。梅蘭芳那個時候去國外,西方人至多是抱著一種獵奇心態,看看男人怎麼演女人,還是一種欣賞玩物的心理,不會有人格的敬重。新中國的藝術訪問團不一樣,西方人看到了一個個獨立、自信、積極的中國人,特別是女性,同時期西方大量人還認為中國婦女纏足、男人都是大煙鬼,主人公用自身經歷,使西方人相信了一個被賣來賣去的孤兒,可以在紅色中國成為讓人敬重的藝術家。這背後所蘊含的宏大歷史敘事,無需多言,事實放在那裏,在我們尚不富裕的時期,中國人的國際形象是令人仰視的。試想,親身經歷過那段歲月的人,怎能忍心忘懷?而這樣的記憶應該一直保留下去,新時代提出“四個自信”不是無源之水,我們有這個底氣。
3.作品完成用了多少時間,創作中最大的挑戰是什麼?
《金甌曲》構思大概要回溯到十年前,恰恰是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時間節點。文藝為人民是我的信念,“兩個結合”重要思想如何落地,是我這幾年的苦苦冥思,《金甌曲》算作一個階段性作業,現在到了交卷的時刻。
小說是藝術作品,藝術性第一,不能簡單地把一些回憶拼湊起來,也不能流於哲學化表達。這個期間,除了採訪,更多需要做資料搜集工作,我信奉作品動人必須細膩,我是80後,怎麼呈現出五六十年代的生活質感讓人信服,這是寫作最需要攻克的。面對老者講述、浩如瀚海的文獻、文物,我必須把這一切賦予生命溫度,讓素材活起來,讓今天的年輕人可以瞭解歷史,也讓那些親歷歷史的人不覺得虛假,這個過程花費了最多的心血。舉例來說,故事的主要發生地在北京,中國城建的迭代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,十年前的地方都會面目全非,為了保證藝術質感,僅北京地圖我就找到了五種版本,從民國初年到70年代末,同一條胡同改名多少次,我不允許這裏有絲毫硬傷,每一處都經過嚴苛考證。說句不客氣的話,拿著《金甌曲》可以做北京city walk的參考。這種做法貫穿了全書,1968年萃華樓一道溜肝尖賣多少錢,書裏寫的都是准的。
4.如果讓你給《金甌曲》一個歸類,你會怎麼劃分?
伊耆:今天流行給文學貼標籤,大女主、勵志、恩怨情仇等等,成熟的文學作品不能是單一性的,必須是多維度,讓1000個讀者誕生1000個哈姆雷特。如果要貼標籤,那《金甌曲》怕是能把所有標籤都沾上。這部作品可以當作歷史小說讀,可以當作女性小說讀,可以當作政治小說讀,也可以當作行業小說讀,還可以當做民俗小說讀......不同的視角,都會從中得到不同的答案。
文學作品的基點是人性,一部好作品必須塑造出讓人留有印象的人物形象,《金甌曲》有名有姓的人物數十位,沒有一個絕對的惡人,也沒有完人,這不是瑪麗蘇文學,女主人公同樣有弱點、有缺陷,有人性幽暗的發微,我是希望讀者看過後,能記住其中某一個人物。未必是主角,很可能是配角,甚至相對負面的人物,這樣的角色更接近常人。畢竟主人公是屬於今天常說的成功人士那一類,是吃到時代紅利的人,多數人沒有這份幸運,在跌宕起伏的歷史洪流和個人命運面前,普通人的選擇更能引起共鳴。
作為作者,無法給這部作品一個詞做主題,它的內涵深度和廣度是足夠的,我更期待有人總結出和我心意相通的主題詞。如果硬控一個詞,我還是選擇好看。我從來不認可純文學的概念,那不過又是小知識份子意淫的快感罷了,小說是通俗文藝,好看是第一位的,至於其他的生髮,留待閱讀後給人遐想,如果寫得不好看,人家連讀下去的欲望都沒有,談什麼都是假的。對於可讀性,我是敢打包票的,沒有兇殺、穿越,似水流年的故事一樣充滿張力!
至於說“三十年後力扛《霸王別姬》”,這句話我自己無法回應,還是交給讀者和時間來檢驗,我是有十足的信心接受檢驗,按老戲班的話說:臺上見!
5.在修仙、穿越、懸疑題材大行其道的時候,你為什麼選擇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,會不會擔心不符合今天的流量需求?
伊耆:作品也有各自的命運,從動筆開始寫作那一刻起,作家肯定要考慮出版,我沒有那麼超凡脫俗,一個從事文藝工作的人如果失去了名利之心,也就別幹這行了。《金甌曲》是我第一本書,新人總是充斥各種困難的,何況這個題材是不是能被出版社接受,我也是茫然的。
選擇京劇藝人這個群體寫作,不是沒有顧慮,但作者不能自束手腳,我始終堅信好作品的魅力是永恆的,看一個作家水準不在於寫什麼,而是怎麼寫?而時代風氣又充滿了變化,最近幾年,在年輕世代中傳統文化自覺升溫,90後、00後是一百多年來最有文化自信的一代人,今天的京劇演出市場,年輕觀眾已是絕對的主力。作為職業媒體人,我的嗅覺是靈敏的,這種變化也讓我有了寫下去的信心。
走到今天,中國到了必須實現文化復興的時刻,這是回避不了的課題,知識份子的責任擔當也讓我必須拿起創作之筆。“兩個結合”重要思想是我們文藝創作者的指路明燈,事在人為,書中我也大膽觸碰了某些所謂的敏感話題,甚至是對中國文學四十年來某種敘事習慣的憤然挑戰。
既然寫的是新中國前30年,特別是京劇界,不可能不涉及政治運動。自70年代末“傷痕文學”出現,對於那段歷史,形成了控訴式的一邊倒敘事,給人以凡是運動衝擊到的人都是被迫害的,但事實真是如此嗎?
時代的埃塵怎麼變成了個人頭上的一座山?這不是簡單粗暴的受害者與加害者模式,人性的幽暗與命運的無常,在大風大浪面前,表現得尤為突出。書中的男性角色,著墨最多的是貫芝荃,他和主人公卞慕雲恩恩怨怨幾十年,貫芝荃最終淪為右派,後半生在抑鬱沉淪中度過,卞慕雲的表現,按照文壇慣性表達,就是恩將仇報,政治扭曲人性。在我真實觸碰到那段歷史的時候,我愈加發現實際情況遠比這種二元對立複雜。事後的受同情者,也是當初萬人唾棄的對象,而高層的初心也會在基層執行中,交雜著個人算計而變異。再比如珠峰這個人物,也擺脫了長久以來對於造反派的刻板塑造,他本是有前途的青年演員,無心捲入了政治旋渦,他有野望,但又堅守著底線,最終成為悲劇人物。
“傷痕文學”出現後,站在那個立場的“人性說”成了文壇主流,現在有所鬆動,年輕一代對那段歷史的看法已經不同於上一輩人,但還缺乏一部正面回擊“傷痕文學”的作品出現,《金甌曲》算是打響了第一槍。
至於流量,我始終認為,不能追隨。因為流量瞬息萬變,創作有週期,你永遠跟不上流量的變化,不問青紅皂白地追求流量,只能把自己搞得面目全非,最後什麼也落不到,這不是創作者應有的心態。文學要讓人成熟、健全,首先作者就要有這方面的素質,要相信文章有價,好作品不論什麼題材,是會被看見的!
為什麼選擇在香港出版,你對香港有什麼樣的印象和情緣?
選擇在香港出版,自然有香港的地緣優勢。作為中國與世界溝通的窗口,香港幾十年的作用毋庸置疑,這裏是貿易、金融的自由港,同樣是思想文化的交匯碰撞之地。在京劇界也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,香港的演出現場是最火爆的,比京津滬這種京劇大碼頭,劇場氛圍都熱烈,當年從上海、天津跑來的那批遺民把京劇帶到了這裏,讓廣東人不聽京劇在香港成了例外。對於我們80後一代,香港文化的影響是至深的,我們是伴隨香港流行文化成長起來的,金庸的小說讓每一個華人少年都種下了俠客夢,流行音樂、電影、TVB電視劇把我們這代人喂大,我至今也懷念香港文化的黃金歲月。
我本人也結識過香港的老輩明星、實業家、媒體人,說到文學,京劇題材在華人世界裏首先想到的是電影《霸王別姬》,而小說原作正是香港作家。當今的香港作家我有兩位很欣賞的,一位年長的是董橋,他的散文有中國傳統文風,是我時常翻閱的枕邊書;年輕一輩裏我喜歡葛亮,評論界說他是年輕軀體裏住著一個老靈魂,我比葛亮還要小幾歲,同樣住著一個老靈魂。《金甌曲》的內容、文風和葛亮的作品很接近,可以劃入同類,我也希望和香港作家做一番藝術較量。在香港出版的《伶人往事》同樣寫京劇藝人,同樣寫新中國前30年,章詒和打的是歷史散文,同類故事,看完《金甌曲》讀者會得出相左的結論,因為我們的立場、視角是相反的,這也是香港寬鬆的環境提供了這樣一個比拼的條件。
香港的出版面對著整個華人世界,相比大陸,發出不一樣的聲音更有可能,我希望《金甌曲》借著香江的海風,吹遍華語文壇。
7.能談一下你接下來的創作計畫嗎?
伊耆:在《金甌曲》寫作接近尾聲時,我的“伶人三部曲”計畫就成型了,現在更加清晰。一百多年來,與國運關係最緊密的文藝載體就是國劇,從進入皇宮那一刻,京劇和京劇藝人的宿命就註定了,擺脫了草根氣息,和國家緊緊捆綁在一起,“伶人三部曲”是借國劇百年沉浮,鉤沉起百年國史的另一個側面。另外兩部作品時代背景分別設置於當下和民國,當代題材借一個京劇團的故事展開對時下熱點的諸多剖析,比如文藝體制、反腐、飯圈現象、網路暴力等等,這會是以第一人稱視角切入,90後一代傳統文化從業者的困境與突圍,基本框架已經搭建起來。另一部民國題材,故事放置在上海一座劇場,圍繞劇場發生的悲歡離合、人生歧路,準備寫到抗美援朝上海京劇界義演捐獻飛機。
三部曲之間有著微弱的聯繫,比如《金甌曲》的主人公卞慕雲,我會讓她在當代題材裏以老藝術家身份出現,也會涉及空巢老人話題,以及對演員這個職業的思考。現在的演員好像只是一個供人娛樂的工具,甚至只有明星,沒有演員,這是時代的悲哀。老藝人拼盡畢生,就是要獲得敬重與認可,而當下的文藝界似乎一夜退回解放前,這裏面有很值得探討的地方。
我心裏也有關於香港題材的創作計畫,現在有兩個初步想法,一個是想寫十八大以來反腐敗對香港的影響,大陸的很多故事,和香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。另一個想寫60年代的香港,那個左翼思潮風起雲湧的香港,這個還需要做很多準備工作。
飯要一口口吃,書也要一筆筆寫,我心中的計畫還是蠻多的,雖然在文壇上,我屬於晚熟的人,但後勁也足,寫作於我已是生命,過去二十幾年的積累似乎都是為了現在的啟航。非常感謝你今天的採訪,期待媒體界、評論界對《金甌曲》發出真知灼見,願聆金石之聲。
欢迎分享转载→ https://www.gangaozaixian.cn/tupian/272.html
Copyright © 2022 港澳在线 All Rights Reserved.京ICP8544814